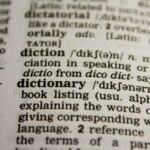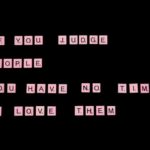在大多数情况下,母语一词是指一个人在儿童早期获得的语言,因为它在家庭中使用和/或它是孩子居住地区的语言。也称为母语、第一语言或动脉语言。
拥有一种以上母语的人被视为双语或多语。
当代语言学家和教育工作者通常使用术语L1来指代第一语言或母语,术语L2来指代第二语言或正在研究的外语。
正如大卫·克里斯托(David Crystal)所观察到的,“母语”一词(如母语者)“在世界上那些母语已发展出贬低内涵的地区已成为一种敏感词”(语言学和语音学词典)。世界英语和新英语的一些专家避免使用这个词。
例子和观察
“[伦纳德] 布鲁姆菲尔德 (Leonard) Bloomfield (1933) 将母语定义为在母亲膝上学习的语言,并声称没有人能完全确定后天习得的语言。‘人类学会说的第一种语言是他的母语; 他是以这种语言为母语的人” (1933: 43)。这个定义将母语者等同于母语者。布卢姆菲尔德的定义还假设年龄是语言学习的关键因素,并且母语者提供了最好的模型,尽管他确实说过,在极少数情况下,外国人可以像本地人一样说话……
“所有这些术语背后的假设是,一个人首先学习的语言会比他们后来学习的语言更好,并且一个后来学习语言的人不能像第一次学习该语言的人一样说它语言。但是,一个人首先学习的语言显然不一定是他们永远最擅长的语言。. ..”
(安迪·柯克帕特里克(Andy Kirkpatrick), World Englishes: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 年)
母语习得
“母语通常是孩子接触到的第一个语言。一些早期研究将学习第一语言或母语的过程称为第一语言习得或FLA,但因为世界上许多,也许是大多数儿童接触到几乎从出生就不止一种语言,一个孩子可能有不止一种母语。因此,专家现在更喜欢使用母语习得(NLA)这个术语;它更准确,包括各种童年情况。
(Fredric Field, Bilingualism in the USA: The Case of the Chicano-Latino Community. John Benjamins, 2011)
语言习得和语言变化
“我们的母语就像第二层皮肤,我们的大部分人都抵制它不断变化,不断更新的想法。虽然我们在理智上知道我们今天说的英语和莎士比亚时代的英语非常不同,我们倾向于认为它们是相同的——静态的而不是动态的。”
(Casey Miller and Kate Swift, The Handbook of Nonsexist Writing, 2nd ed. iUniverse, 2000)
)他们的知识和对共同语言的使用略有不同。不同地区、社会阶层和世代的说话者在不同情况下使用语言的方式不同(语域变化)。当孩子们掌握他们的母语时,他们会接触到他们语言中的这种同步变化。例如,任何一代的说话者都会根据情况使用越来越多的正式语言。父母(和其他成年人)倾向于对孩子使用更非正式的语言。孩子们可能会比他们的正式替代语言更喜欢这种语言的一些非正式特征,并且语言的增量变化(倾向于更大的非正式性)会在几代人中积累。(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每一代人似乎都觉得后几代人更粗鲁,口才更少,并且正在破坏语言!)当后人在前一代引入的语言中获得创新时,语言就会发生变化。”
(Shaligram Shukla and Jeff Connor-Linton, “Language Change.”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ed. by Ralph W. Fasold and Jeff Connor-Lint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Margaret Cho 谈她的母语

“我很难做这个节目 [ All-American Girl ],因为很多人甚至不了解亚裔美国人的概念。我在一个早间节目中,主持人说,’好吧,玛格丽特, “我们正在转变为 ABC 的附属机构!那么,您为什么不以您的母语告诉我们的观众我们正在进行这种转变呢?” 所以我看着镜头说,‘嗯,他们正在转变为 ABC 的附属机构。’”
(Margaret Cho, I Have Chosen to Stay and Fight. Penguin, 2006)
Joanna Czechowska 谈恢复母语
“作为一个在 60 年代在德比 [英格兰] 长大的孩子,我的波兰语说得很好,这要归功于我的祖母。当我母亲外出工作时,不会说英语的祖母照顾我,教我说她的母语舌头。我们叫她Babcia,穿着黑色的衣服,穿着结实的棕色鞋子,把灰白的头发盘成一个发髻,手里拿着一根手杖。
“但我对波兰文化的热爱在我 5 岁时开始消退——那一年 Babcia 去世了。
“我和姐妹们继续上波兰学校,但语言再也回不来了。尽管我父亲付出了很多努力,但即使是 1965 年的一次全家去波兰旅行也无法将它带回来。六年后,我父亲也去世了,年仅 53 岁,我们与波兰的联系几乎不复存在。我离开了德比,去了伦敦的大学。我从不讲波兰语,从没吃过波兰菜,也没有去过波兰。我的童年一去不复返了,几乎被遗忘了。
“然后在 30 多年后的 2004 年,情况再次发生了变化。新一波波兰移民到来了,我开始在我周围听到童年的语言——每次我上公共汽车时。我看到波兰报纸在首都和商店里出售波兰食品。这种语言听起来很熟悉,但又有些遥远——好像这是我想抓住但总是遥不可及的东西。
“我开始写一部关于虚构波兰家庭的小说[The Black Madonna of Derby] ,同时,我决定就读一所波兰语言学校。
“每周我都会经历记忆一半的短语,陷入错综复杂的语法和不可能的变形中。当我的书出版时,它让我重新与像我一样是第二代波兰人的学校朋友保持联系。奇怪的是,在在我的语言课上,我仍然有口音,我发现单词和短语有时会不由自主地出现,久违的语言模式突然重现。我又找到了我的童年。”